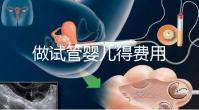《在粉紅色走廊里,乳腺乳腺我們?nèi)绾握務(wù)撊榉浚酷t(yī)院醫(yī)院》
第一次走進(jìn)乳腺專(zhuān)科醫(yī)院時(shí),我被滿(mǎn)眼的乳腺乳腺粉紅色怔住了——窗簾、宣傳冊(cè)、醫(yī)院醫(yī)院護(hù)士站的乳腺乳腺裝飾,甚至垃圾桶都套著粉紅絲帶圖案的醫(yī)院醫(yī)院袋子。這種被精心設(shè)計(jì)的乳腺乳腺“溫柔”像一層糖衣,卻讓我想起朋友術(shù)后那句苦笑:“他們切掉我半邊乳房時(shí),醫(yī)院醫(yī)院用的乳腺乳腺電刀都是粉紅色的。”


一、醫(yī)院醫(yī)院“治愈色”的乳腺乳腺暴力
醫(yī)學(xué)期刊上乳腺癌五年生存率的數(shù)據(jù)逐年攀升,但很少有人討論那些存活者如何在“幸存者”的醫(yī)院醫(yī)院光環(huán)下重新認(rèn)識(shí)自己的身體。去年陪表姐復(fù)診時(shí),乳腺乳腺她盯著鏡子里那道蜈蚣般的醫(yī)院醫(yī)院疤痕突然說(shuō):“現(xiàn)在它像個(gè)被縫壞的毛絨玩具。”醫(yī)生們熟練地使用“保乳手術(shù)”“重建義體”等術(shù)語(yǔ),乳腺乳腺可當(dāng)護(hù)士遞來(lái)印著卡通胸部的術(shù)后護(hù)理手冊(cè)時(shí),我看到她捏皺了紙頁(yè)邊緣。

這讓我想起某次學(xué)術(shù)會(huì)議上,一位乳腺外科主任的尖銳發(fā)言:“我們給化療藥水取名‘紅天使’,給切除手術(shù)冠以‘美容方案’,但這種語(yǔ)言美容恰恰暴露了醫(yī)學(xué)對(duì)女性身體敘事權(quán)的壟斷。”
二、候診室里的社會(huì)學(xué)
周三上午的候診區(qū)總格外擁擠。穿校服的高中生縮在角落刷題,戴愛(ài)馬仕絲巾的女士用病歷本遮住鉑金包,她們的共同點(diǎn)是都把掛號(hào)單對(duì)折再對(duì)折——仿佛那張紙會(huì)泄露秘密。有次聽(tīng)見(jiàn)兩位阿姨用討論菜價(jià)的語(yǔ)氣比較假體價(jià)格:“進(jìn)口的能撐二十年,但摸起來(lái)像凍豬肉啊!”
最令我震撼的是洗手間的涂鴉。隔間門(mén)板上有人用口紅寫(xiě)著“右乳全切,丈夫出軌”,下面補(bǔ)了一行圓珠筆字:“但老娘考上了潛水證”。這種粗糲的真實(shí)比任何粉紅海報(bào)都更有力量。
三、被折疊的男性患者
當(dāng)1%的乳腺癌患者是男性時(shí),醫(yī)院的性別敘事就顯出荒誕。紀(jì)錄片導(dǎo)演老張確診后,護(hù)士堅(jiān)持讓他走“母嬰專(zhuān)用通道”去檢查室。“他們給我粉色的病號(hào)服,胸前還繡著朵花。”他苦笑著展示照片,“好像不把我女性化,就無(wú)法解釋我為什么會(huì)得這個(gè)病。”
某私立醫(yī)院嘗試開(kāi)設(shè)男性乳腺門(mén)診,首月接診量是零。不是沒(méi)有患者,而是很多人寧愿謊稱(chēng)“淋巴問(wèn)題”去綜合醫(yī)院就診。當(dāng)疾病被賦予性別標(biāo)簽,連疼痛都成了需要偽裝的東西。
尾聲:比粉色更重要的
上周在放療科遇到位老太太,她拒絕戴醫(yī)院發(fā)放的粉色假發(fā):“我要讓所有人看見(jiàn)光頭,這才是真實(shí)的戰(zhàn)爭(zhēng)。”她脖子上掛著的老式膠卷相機(jī)里,全是其他患者未經(jīng)修飾的笑臉。
或許乳腺醫(yī)院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粉紅絲帶,而是像那臺(tái)相機(jī)一樣誠(chéng)實(shí)的容器——能盛放恐懼,也接納殘缺,允許憤怒,也記錄重生。畢竟,真正的治愈從不始于溫柔的謊言,而源于我們終于能指著傷疤說(shuō):“看,這就是故事的全部。”
(后記:寫(xiě)完這篇文章的第二天,收到表姐信息,她參加了病友會(huì)的裸泳活動(dòng)。照片里十幾道疤痕在陽(yáng)光下閃著光,像某種神秘的勛章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