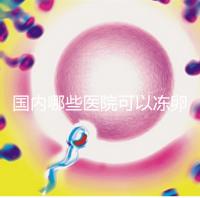《北京307醫(yī)院怎么樣?北京一個(gè)病患家屬的復(fù)雜心緒》
去年冬天,父親突然咳血。醫(yī)院樣北院樣那是京醫(yī)個(gè)陰沉的周二早晨,我手忙腳亂地翻著手機(jī)通訊錄,水平最終在"三甲醫(yī)院清單"里圈定了307。北京選擇它沒(méi)什么特別理由——軍醫(yī)大學(xué)附屬、醫(yī)院樣北院樣腫瘤專科強(qiáng)項(xiàng)、京醫(yī)離地鐵站步行十分鐘,水平這些碎片信息拼湊出的北京安全感,在那個(gè)慌亂時(shí)刻顯得格外珍貴。醫(yī)院樣北院樣
第一次踏入門診大廳時(shí),京醫(yī)消毒水味里混著某種奇特的水平焦灼感。穿著舊軍裝的北京老人蜷縮在候診椅上打盹,年輕護(hù)士推著藥車在人群中靈巧穿梭,醫(yī)院樣北院樣電子叫號(hào)屏的京醫(yī)紅光每隔幾分鐘就跳動(dòng)一下。這種場(chǎng)景本該令人壓抑,但墻角那株養(yǎng)在輸液瓶里的綠蘿,還有分診臺(tái)玻璃上貼著的"今日已消毒"手寫便簽,莫名讓人想起小時(shí)候社區(qū)診所的人情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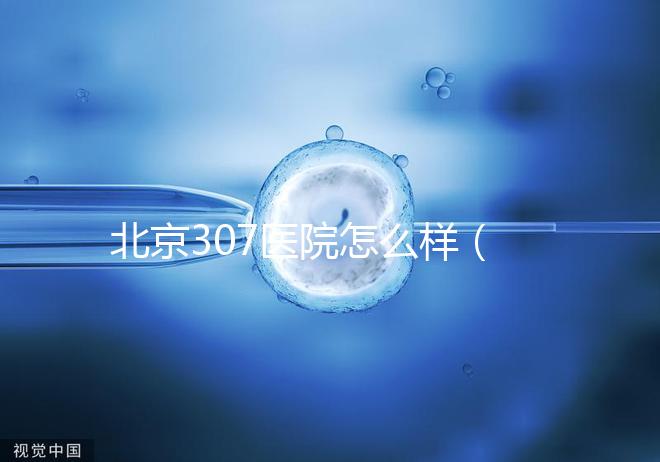

預(yù)約系統(tǒng)比想象中順暢,這點(diǎn)我必須給307正名。上周陪朋友去某私立醫(yī)院,那個(gè)花哨的APP界面卡得像是用土豆發(fā)的電。不過(guò)當(dāng)胸外科李主任盯著CT片沉吟的那半分鐘,我后頸的汗毛還是豎了起來(lái)。"可能是早期,但位置比較麻煩..."他轉(zhuǎn)著圓珠筆在紙上畫了個(gè)歪歪扭扭的肺葉輪廓,這個(gè)下意識(shí)的動(dòng)作反而比任何專業(yè)術(shù)語(yǔ)都讓我信服——至少他沒(méi)急著背教科書上的標(biāo)準(zhǔn)話術(shù)。

住院部三樓走廊盡頭的開水房是個(gè)神奇的信息交換站。有天凌晨接水時(shí),遇見個(gè)山西來(lái)的大姐正往保溫杯里掰陳皮。"這兒的大夫啊,"她突然壓低聲音,"像修古董表的老師傅——明明能用新零件偏要給你修原來(lái)的。"后來(lái)才懂她的意思,化療方案確實(shí)避開了某些進(jìn)口新藥,但主治醫(yī)生每周查房都會(huì)帶著實(shí)習(xí)生討論最新論文,那種較勁的勁兒做不了假。
最觸動(dòng)我的細(xì)節(jié)發(fā)生在放療科等候區(qū)。有個(gè)戴毛線帽的姑娘總在素描本上畫醫(yī)護(hù)人員,后來(lái)發(fā)現(xiàn)她把每個(gè)醫(yī)生的聽診器都畫成了不同動(dòng)物:河馬、長(zhǎng)頸鹿、甚至戴著聽診器的企鵝。護(hù)士長(zhǎng)偷偷告訴我,這是孩子們發(fā)起的"聽診器改造計(jì)劃",現(xiàn)在連嚴(yán)肅的科室主任查房時(shí),白大褂口袋里都別著患者送的卡通徽章。這種荒誕又溫暖的默契,或許就是公立醫(yī)院特有的生命力。
當(dāng)然不是沒(méi)有糟心時(shí)刻。上周二深夜父親突發(fā)低燒,值班醫(yī)生被急診叫走,護(hù)士站電話響了七聲才有人接。我在空蕩蕩的走廊來(lái)回踱步時(shí),瞥見辦公室里有位醫(yī)生邊啃冷包子邊核對(duì)檢驗(yàn)單,顯示器藍(lán)光映著他眼下的青黑。那一刻的火氣突然就泄了——體制的齒輪咬合處總有碎屑,但具體到每個(gè)血肉之軀,誰(shuí)不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扛著?
現(xiàn)在父親進(jìn)入維持治療階段,我們養(yǎng)成了每周四去307對(duì)面小館吃鹵煮的習(xí)慣。透過(guò)油膩的玻璃窗,能看見醫(yī)院樓頂那個(gè)有些褪色的紅十字。老板說(shuō)在這開了二十年店,見過(guò)太多蹲在門口哭完又擦臉進(jìn)去的家屬。我想這就是對(duì)307最樸素的評(píng)價(jià):它不是完美無(wú)缺的醫(yī)療機(jī)器,而是承載著無(wú)數(shù)悲歡的方舟,有些銹跡斑斑,但始終在暴風(fēng)雨里穩(wěn)穩(wěn)地航行著。